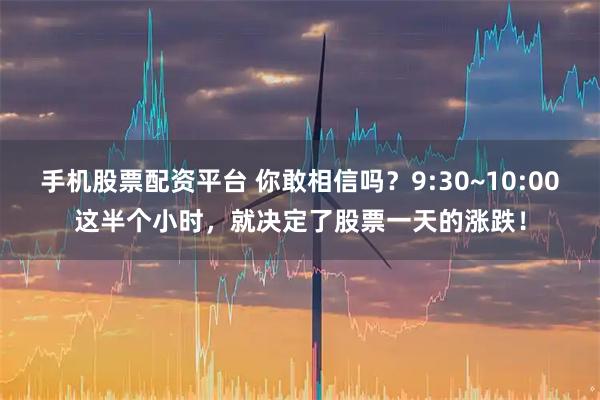“1971年5月1日,张参谋长,你怎么也在这儿?”天安门城楼的风掠过红旗在线配资交易·加杠网,半眯着眼,抬手冲张震打了个招呼。四周喧嚷,人流如潮,两位久别的老战友却像突然被定格,一瞬间只剩彼此。
张震没想到会在游行观礼队伍里遇到邓子恢。他握住邓老的手,只觉仍是当年那股劲道,仿佛转身就能回到淮北的密林与村庄。寒暄不过几句,邓子恢便邀他翌日来家里吃午饭,说要好好聊聊长江工程和农村的新情况。

第二天中午,北海公园西畔的一处老式四合院里,菜不多,都是家常:醋溜白菜、红烧鲫鱼、酱牛肉。邓子恢夹起一块牛肉:“农村要稳,先得让群众兜里有余粮。”他说得爽朗却笃定。张震点头,又担心邓老爱直言会惹事,小声提醒:“情况复杂,您先等等。”邓子恢摆摆手:“怕啥,调研清楚再上书,还是老规矩。”
一次饭局,本是老友叙旧,却成了两人最后的谋面。翌年冬天,北京飘起第一场雪,张震在武汉听到邓老住院的消息,既想即刻动身,又被手头军工任务拖住,只能托人捎去一封慰问信。没等回信,电波里便传来12月10日的噩耗。张震呆立良久,胸口像被什么重物压住,说不出话。
若将时针拨回三十多年前,1938年皖南岩寺小镇的一间旧祠堂,两人第一次见面同样难忘。那时张震是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,正忙着整编部队,邓子恢受陈毅委托来检查工作。祠堂门口泥泞不堪,邓子恢卷袖挽裤,脚上满是泥巴,进门一句“部队伙食咋样?”让张震先愣后笑:原以为留过洋的“大秀才”必然书卷气十足,哪想到是个地道“老农民”。

邓子恢年长十八岁,却毫无架子。工作会议一结束,他拉着年轻干部下连队,蹲在灶台边尝了两口红薯糊糊:“没油盐,再咸点能好入口。”晚上住农家,炕窄,他索性往地铺一躺,呼噜声此起彼伏。张震日后说,正是那几夜,让他明白何谓“与士卒同甘苦”。
除了亲民,邓子恢的谋略更令人佩服。1942年,四师在淮北打游击,部队缺衣少粮,地方税收也被日伪层层盘剥。邓老提出“打通敌后贸易”的主意:盐、布、棉花大胆卖到徐州、蚌埠,再换回药品钢材。拍桌称快,张震则负责护送商队。短短半年,淮北根据地粮食储备翻了一倍,部队士气大振。
抗战胜利后,华中、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,邓子恢出任分局书记。面临数千万群众靠谁养活的棘手问题,他又把旧时在闽西搞粮食互济社的经验搬了出来:先扶持贫农种口粮,再鼓励富裕中农出手流贷。一年之内,缺粮最严重的泰兴、如皋出现余粮返销现象。陈毅拍拍他的肩:“邓老,这一招阔了咱的心。”

1953年,中央决定成立农村工作部,毛泽东一句“找邓子恢来”拍板定人选。那时不少干部只知道他留过日,却不知道他祖祖辈辈种田。进京开会,他仍旧蓝布中山装,袖口洗得发白,兜里揣把小算盘。一次汇报,他干脆掏出一包稻种放到桌上:“稻谷是人民的命根子,部里首要任务是保证它不出问题。”众人哑然,随即鼓掌。
然而,实事求是的性格注定与“左”的风潮冲突。农村合作化过猛,他多次建言“循序渐进”。1957年之后,机关里对他有些微词,他却依旧到河南、安徽蹲点。同去的年轻人后来回忆:邓老坐牛车,饿了就啃冷馒头,不停询问“今年田里亩产多少”“猪圈有几头猪”。他把调查本塞进腰包,说:“还是地里这点东西最让人踏实。”
转眼来到1971年的那顿家常饭。席间,邓子恢提起正争论不休的葛洲坝方案:“修坝可以,但大江通航不能误。”张震看着这位老人,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敬服。谁能想到,这个谈起三江分洪和高峡平湖同样兴奋的人,半年后竟被确诊为胰腺癌。治疗期间,他还让秘书代笔,一封又一封把农村试点的情况寄往国务院。

12月14日的追悼会上,周恩来总理神情凝重,挽联只有十六字:鞠躬尽瘁,实事求是;高风亮节,民本情怀。张震没能到场,只能在武汉军区礼堂默哀。灯光昏黄,他想起闽西密林里那支没油盐的红薯糊糊,想起淮北夜行商队的辘轳声,也想起天安门城楼邓老爽朗的一笑,心底一酸,眼眶湿润。
二十四年后,他写下《怀念邓子恢同志》寄给中央档案馆,字迹苍劲,却掩不住拳拳之情。晚年接受采访,有人问他何事最憾,他沉默片刻,说:“没赶上送邓老最后一程。”说罢抬头望向窗外,汉江水悠悠,仿佛还在等待那位手持芭蕉扇、脚穿布鞋的老人回到田头。那份未竟的告别,也随江水,一直在他心里流淌。
捷希源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