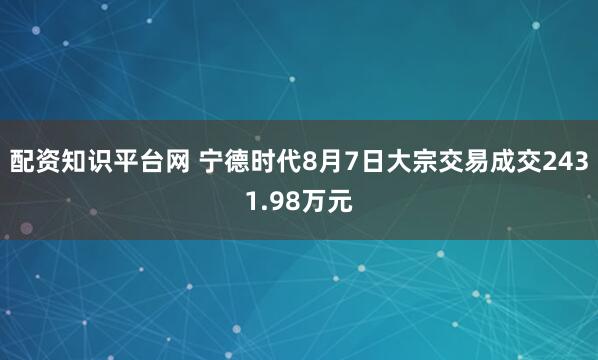【1973年8月股票配资8倍平台,北京人民大会堂后台】 “小邢,你来啦?都16个头衔了吧?”警卫员半开玩笑。邢燕子把草绿色挎包往肩上一甩,笑出虎牙:“别逗了,我还是惦记庄稼地里的苗呢。”一句话,逗得屋里几位代表直乐。
1940年,她出生在北京,父亲给她起乳名“燕子”,只是因为自家窗前常有雨燕掠过。母亲早逝,祖父母住在宝坻乡下。城里有电灯自来水,可小姑娘偏爱田埂上的蚂蚱和沟渠里的蛤蟆,寒暑假往村里钻,脚底板被麦茬划得生疼也不喊。

朝鲜战争爆发那年,她还在天津铁路局子弟小学。班上组织宣传小分队,高声喊“抗美援朝”,燕子嗓门最大。老师常说:“这孩子实心眼,将来要去哪儿?”13岁那年,全家人都劝她继续升学,可她扔下书包回村,“我要在地里闯一闯。”老人直摇头,连同学都笑她傻,她却认准了土里刨食这条路。
回乡第一天就被安排到公共食堂做饭,锅铲比胳膊还沉,200多口人挑剔得紧。她不会切菜,手上磨起泡,夜里疼得翻来覆去。有人递话:“回城找你爸吧,副厂长给闺女找份活轻省。”燕子咬牙顶过一个冬天,学会掌勺,也学会早起劈柴。
1959年涝灾,司家庄千余亩庄稼几乎全泡汤。队里牲口不够,她带着“燕子突击队”硬顶上去:两人架一张犁,肩膀磨破,汗水淌进血口也不吭声。姐妹们累得瘫地上,她一句“不能让水把咱们的种子泡死”,大家又爬起来。那年冬捕,他们从冰窟窿捞出几百斤鱼虾,卖掉后总算让全村熬到了春天。

有意思的是,最先写她的并不是大报。《唐山劳动报》的记者于田去采访另一个典型,半路听到“女娃带队犁地”的事,顺手写了篇短稿。稿子见报,随后《河北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人民日报》接连转载,邢燕子三字忽然成了时代标签。
名气来了,职务也跟着堆上来:大队支书、共青团常委、省妇联委员……算来算去正好16个。有一天她背着帆布包到天津开会,表格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头衔,她自己都数麻了眼。文件报到北京,周恩来看到后批了行字:“中间职务全撤,只保留最低和最高。”最高是中央委员,最低依旧是司家庄党支部书记——一头在天,一脚踩地。
批示一下来,她长舒口气。“还是总理懂我!”回村那晚,乡亲们杀了只老母鸡,她挽起袖子就在炕桌边擀面,嘴里说:“当官不耽误种地,咱得先把麦子管住。”炉火呼啦啦,屋顶结满白霜,村里老人说那是最能暖心的一晚。

1964年,她以第三届全国人大执行主席身份和毛泽东同席用餐。毛主席握着她的手问:“你就是燕子?”她只点头,激动得一句多余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主席安排座位时还回头嘱咐:“别翘尾巴。”这一句,她记了大半生。
改革开放后,宝坻划归天津。1981年,她调到北辰区永新知青综合厂任党委副书记。厂里最脏的养猪场缺人,她卷起裤腿下猪圈,手里攥着饲料勺子,身上却佩着中央委员的胸卡,工人们直乐:这胸卡可不怕臭?她回答:“臭味是粮食味,闻着踏实。”
1987年,当了北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分管城乡建设。有人说“燕子飞高了”,她却天天跑村跑河堤。1995年北运河洪水,她五十多岁,拎着沙袋爬堤坝。机关里年轻干部抬头一看,“老太太也来啦!”一句玩笑,映出她满脸泥水的笑容。

退休后,老人学会用录音机跟着哼京剧,清晨绕小花园快走几圈,回家喝碗小米粥。偶尔路过司家庄,乡亲们指着柏油道说:“那是燕子路。”跨潮白河的大桥也叫“燕子桥”。桥下水流急,她站在岸边揉揉眼眶:“这地方,给过我一辈子的劲头。”
邢燕子走于2022年清晨,81岁。生前她常讲:“我不过是替那代农民露脸。”时代风云早已翻篇,可那份扎根泥土的倔强,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活蹦乱跳。
捷希源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